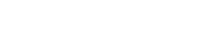红山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席永杰
(赤峰学院院长、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主体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该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与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诸多原始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并使该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史前时期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诸多优势因素被夏商周三代融合吸收,成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回顾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总结红山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找准当前制约红山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确立21世纪红山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回顾
回顾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可分成以下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红山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尚不清楚,田野工作仅限于小规模的地表调查。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到内蒙古林西县和赤峰英金河畔调查,采集到红山文化的陶片和石器标本。1922年至1924年期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多次到内蒙古赤峰地区调查,发现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赤峰红山遗址群。1930年10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内蒙古林西县和赤峰英金河流域调查,并准备在林西县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后因遭遇大雪,发掘计划被迫取消。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到赤峰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在红山文化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资料,梁思永先生认识到西辽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应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并已注意到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成为较长时期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指导性意见。
第二阶段: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第一、二住地进行发掘,获得一批重要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193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日本人所称的第二住地是一处文化性质比较单纯的红山文化居住遗址,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总面积约有2万平方米,房址顺坡势沿西北—东南向排列。日本人当年采用探沟法发掘,没有发掘出红山文化房址,但发现了积满草木灰的灶址。该地点出土遗物十分丰富,精美的彩陶与施以压印、压划纹的夹砂灰褐陶共存,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裴文中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提出“赤峰期”之前有“林西期”,并认为“赤峰期”是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同中原仰韶文化在长城地带接触而形成的“混合文化”。直至建国以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仍旧停留在《赤峰红山后》报告所公布的材料,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外诸多史前考古学家已经形成了共识。
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并由此确立了该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标志性工作有两项:一是195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并指出“红山后的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红山后第二住地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提高了对于红山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
第四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围绕红山文化这一重要课题,对于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三道湾、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遗址的调查和主动性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蜘蛛山遗址的发掘出土一批红山文化典型陶器标本,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汉初四种不同文化时期遗存之间的叠压关系,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西水泉遗址发掘出3座红山文化半地穴式房址,其中一座为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另外两座为面积10余平方米的小型房址,同时出土大量的红山文化陶、石器标本,深化了对于红山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为研究红山文化房屋形制和聚落布局提供了珍贵资料。四棱山遗址发现分布集中、保存较好的6座红山文化窑址,有单室窑和双火膛连室窑之分,是研究红山文化陶器烧制技术的珍贵资料。1971年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1件墨绿色“c”形玉龙,通高26厘米,是迄今所知个体最大的红山文化玉龙。1973年夏季,阜新胡头沟遗址发现了2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出土玉器共18件,红山文化玉器初露端倪。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祭坛的形制。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主体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性祭祀遗址,在各个地点积石冢石棺墓内出土一批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辉煌的红山文化玉雕群最终得以确认,同时还发现女神庙、祭坛、大型祭祀平台等相关遗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敖汉旗西台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的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两道围壕连接成“凸”字形,将房址与窖穴环绕其内,是红山文化聚落考古的重要收获。位于西拉木伦河北部的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一处高规格的红山文化中心性聚落。该遗址共征集、采集到红山文化玉器100余件成为西拉木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为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实证。红山文化玉器综合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真正确立了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敖汉旗文物普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0余处,规模大小不一,小型遗址仅有4000—5000平方米,较大的遗址可达3—10万平方米,最大的遗址竟有2—3平方公里。在综合研究方面,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探索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国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得以建立,红山文化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高。巴林左旗二道梁、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县白音长汗等遗址均发掘出红山文化房址或墓葬,出土一批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199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一书,红山文化玉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
二、21世纪初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
进入21世纪,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发掘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该地点是一处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长方形环壕聚落,填补了红山文化晚期居址研究资料的空白。房址偏小,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大体成排分布,窖穴分布在房址外围,排列密集,充分反映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单一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单元。在21号灰坑内发现1件三人蹲坐相拥陶塑像,外表呈红褐色,三人头部紧抵,背部朝外,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从细腰、大臀等特征看,应为裸体女性。红山文化陶塑业非常发达,牛河梁遗址曾出土过相当于真人三倍大小的人体残块,西水泉、东山嘴等遗址均出土过小型陶塑人像,以女性居多,但均为单体,多体陶塑人像尚属首次发现。
第二,2001年7月,敖汉旗博物馆对草帽山遗址第二地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获得一批红山文化晚期重要的遗迹、遗物资料。该地点清理出分层砌筑的石墙基址,其内分布有方形的祭坛和小型石棺墓,共7座。1号墓内随葬1件方形玉璧和1件石环,7号墓内随葬1件玉环和1件骨笛。在石墙基址的外侧,发现有成排分布的无底筒形陶器,其中1件碎片内壁发现有“米”字形刻划符号。在祭坛的旁边还发现有石雕神像,共有4例,其中1例保存完好,与真人大小相近。草帽山遗址内坛冢结合分布,祭祀功能十分突出,是新世纪红山文化考古较重要的收获。
第三,200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第十六地点进行发掘,发现1座大型石棺墓(M4)。墓穴呈长方形,在山体最坚硬的变质花岗岩的岩脉上开凿而成,北侧呈斜坡状并起台阶,其余三侧陡直。圹穴内砌筑石棺,棺壁用17层石板叠砌而成,内壁非常整齐,顶盖用条状石板搭封,底部平铺整齐的石板。圹穴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墓底距地表深5.22米。墓主人呈仰身直肢葬,头向朝东,是一位45—50岁左右的成年男性。墓内出土玉凤、箍形器、人各1件、玉环3件,还出有2件绿松石坠饰。从出土位置看,玉凤横置在墓主人头骨顶部下侧;箍形器放置在右侧胸部;玉人和两件玉环出自左腹下侧,两件玉环相叠放置;还有1件玉环佩戴在墓主人右臂上。这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格最早的一座红山大型墓葬,虽未见勾云形器,但和箍形器共出的有玉人和玉凤,代表了一种新型的高规格玉器组合关系,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和用玉制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21世纪红山文化研究展望
红山文化的发现已有近70年的历史,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方面均已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深入开展红山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同时也应看到,红山文化研究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红山文化目前分为四期,年代跨度约为1500年,目前三、四期的资料较丰富,一、二期的资料明显偏少,需要有意识加强寻找、发掘红山文化早期遗存,以便建立更完整的红山文化自身发展序列。
第二,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目前缺乏经过较大规模揭露的居住性遗址,对房屋形制、聚落布局、社会组织形态的认识尚显薄弱。
第三,红山文化积石冢多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具有鲜明的宗教祭祀意义。埋葬在积石冢石棺墓内的死者仅限于少数社会成员,推断生前应为享有特权的祭司阶层,死后多用玉器随葬,有关普通社会成员的完整墓地至今尚未发现,在墓葬形制及随葬方式等方面有无差异尚待证实。
第四,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狩猎、采集和捕捞经济作为补充,但尚缺乏植物考古证据。
第五,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理论问题学术界争论颇多,需要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中寻找更有力的证据。
针对上述薄弱环节,开展富有成效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相信21世纪的红山文化研究必将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