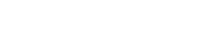回顾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史,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红山文化发现到70年代末的大约半个世纪时间里,红山文化一直是作为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一支边远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中属于“一带而过”的角色。80年代以来它的异军突起,当然主要是在辽宁西部的东山嘴特别是牛河梁,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和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提出了辽西地区5000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也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从距今4000年前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并将目光从中原更多地移向中原以外地区。因为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程度的深入,也使参予研究的学者的范围远不限于历史考古界,形成社会各界关注并向专业界反馈起到推动作用的形势。尽管目前对红山文化等诸多距今5000前后的史前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仍有各种不同意见,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仍然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由红山文化等考古新发现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一如继往地在不断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始终是这一课题研究中举足轻重的部份。由红山文化本身的社会变革引伸到对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探索,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我在《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讨论会论文,2000年)一文中,提出了5个方面:积石冢所具有的“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为主的社会分层;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积石冢体现“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女神庙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体现以一人为中心的等级制用宗教形式固定下来;通神及其独占权;最高层次聚落中心的形成。
关于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的探索,是目前理解红山文化跨入文明社会即古国阶段的几个主要方面,它没有涉及到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形成等诸文明要素,却是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为认识基础的,从而也更能反映出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
关于由探讨红山文化社会变革所涉及到的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这里从三个方面谈起。
一.多元与交汇
70年代到80年代初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正确地揭示了中国古文化发展的规律,已成为大多数考古工作者认可的学科指导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从而引发了在各地寻找文明起源的新思路。然而,多元不等于对等,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提出,各区域诸考古文化的发展,既大致同步又不平衡。在这方面,要充分重视中原以外地区文明起源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情况,如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都是文明发达较早且特点较为突出的地区。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提出,各区域诸考古文化间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在频繁交汇中相互促进的,从而作用也是有主有次的。其中,在中华文明起源最关键的五千年前后,也是史前文化交汇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又集中体现为三大考古文化区之间的交汇,即中原文化区、东南文化区和东北文化区。这三大区之间的交汇,从多年的考古发现看,又以东西之间即中原区与东南区和南北之间即中原区与东北区,为主要的两个交汇趋向,它们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影响也最大。
关于东西交汇。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史学界和考古界就已触及到这个问题。史学界有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考古界因近代考古传入中国初期发掘的河南豫西地区仰韶村遗址,有彩陶与黑陶共出现象和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提出西部仰韶文化与东方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和“东西混合说”,以与史学界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以后随着50年代末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得知东方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代相当并有所接触的是大汶口文化,并揭示出先以仰韶文化彩陶对东方史前文化的影响为主,后以大汶口文化“鼎豆壶”对仰韶文化影响为主的东西文化关系。而后者尤以靠近东方的豫西一些中心聚落如王湾、大河村、西山等表现更为明显。特别是被视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最有力证据的陶寺遗址,不仅墓葬陶器中大汶口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而且出现了来自北方和更远方的良渚文化的因素,从而使陶寺文化具有了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多元综合体性质。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汇特别是东方区对中原区的影响,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地区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史前时期的南北交汇也提出较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长城地带北沿发现的锦西沙锅屯和赤峰红山后这两处遗址,石器和陶器所具有的中原与当地两种文化因素既共存又极易区别。梁思永、尹达、裴文中诸先生都以为这是长城南北史前文化交流接触的反映。1930年,梁思永先生就提出东北的西南部是长城以北细石器文化与长城以南彩陶文化的接触地区:“安特生沙锅屯的发现已暗示解决地层问题的方向。绳纹陶器及彩色陶器之出现于热河南部与辽宁南部极明白的指示,给我们解决地层问题的地方。在‘沿边文化接触区域’作发掘工作”。40年代,裴文中也认为,这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南下,与仰韶文化北上,在长城地带接触而产生的混合文化;50年代初,尹达在梁思永的建议下,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将红山文化列为一章,以为这是南北文化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文化:
“就这一新石器时代遗址(赤峰红山后)陶器的特征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新石器的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在陶器上的特点,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着色陶器的特点。因之,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似应为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的文化遗存”,并建议称为“红山文化”。可知,红山文化的定名,就同南北史前文化的交汇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文化关系的研究,在80年代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有一个飞跃,那就是认识到,这一南北交汇大大促进了辽西区文明起源的进程。
由于红山文化分期及其与仰韶文化早晚对应关系研究的进展,已可分辨出这一南北交汇是有一个前后过程的。约距今6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对东北区南部红山文化的影响,表现为红山文化早期出现具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红顶碗”并促成了红山文化的形成。约距今5500年前后,红山文化一方面仍然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形成具南北两种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一方面随着自身的强大而南下,在燕山南麓出现南北两种文化的碰撞。后者的证据是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壶流河流域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箆点之字纹陶器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绘龙鳞纹图案彩陶垂腹罐在桑干河上游有共存关系。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山西省侯马召开的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并提出,辽西地区作为五千年古国象征之一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南北文化碰撞产生的“文明火花”。以后他并具体论证了这一文化交汇的路线、对接点、形式及后果:
“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划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
以上可见,多元与交汇是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一大特征。
二.通神为礼
无论东西交汇导致“鼎豆壶”在中原地区的出现,还是南北交汇在辽西地区产生的“坛庙冢”,都已涉及到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虽然观点各异,但已经达成若干共识,其中最为紧要的一个共识是,人与人的关系导致国家产生,是文明起源的核心问题,而礼是对中国古代人与人关系最集中的反映,所以礼的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息息相关。考古学上反映礼制的材料是多方面的,既有墓葬及随葬的各类器物,也有建筑组合及制度,是从考古学上追溯礼制起源从而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途径。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代礼制,其起源是与通神的巫术密切相关的,这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一个带有阶段性意义的新认识,而这一认识的取得,最初就是从红山文化的新考古发现的研究中得出的。这指的主要是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群的发现。
70年代末东山嘴遗址发现后,就曾引起考古界对在田野工作中寻找史前祭祀性遗址的广泛关注。牛河梁大规模祭祀遗址群的发现则使长期基础薄弱的中国的史前宗教考古研究在高起点上起步。苏秉琦先生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的1984年就已指出: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当年在这一带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的大建筑群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认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它们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过和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墓群,却连续发现过相当殷周之际的青铜器群窖藏达六处之多。我们有理由推测,这里还有可能发现与窖藏同一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遗迹。这里的‘坛’(东山嘴)、‘庙’(牛河梁)、‘冢’(积石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郊’、‘燎’、‘禘’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天地礼仪的专名,是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推想苏秉琦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不仅视东山嘴、牛河梁为祭祀性遗址,而且已将文明起源与史前祭祀紧密联系起来了。以后他又根据牛河梁女神庙遗址泥塑人像群的塑造,十分讲究写实性的特点:“‘女神’是由五千五百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进一步提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十分明确地将女神庙的祭祀对象定格为祖先神。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这一思路对牛河梁遗址所反映的祖先崇拜进行考察:
一,坛庙冢三位一体的有机组合,相互关联,功能应相近,即都以对祖先的祭祀为主。
二,冢坛结合,同处一冈,是在冢上和冢前设祭,主要祭祀对象必然是墓主人即祖先亡灵,是近祖;女神庙祭祀对象为人的偶像,为远祖。庙为完全不同于积石冢和祭坛的土木结构,又位于主梁顶,并被积石冢环绕四周,处于整个遗址群的中心地位,应是更高的祭祖场所。
三,庙在多室一体的布局内设围绕主神的群神,又远离住地独立营建,已非村落内设“大房子”的氏族祭祀,也为部落一级的祭祀规模所不及,而只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祭祀先祖的圣地,如此规模和规格的祭祖场所,只能是进入祖先崇拜的高级阶段才可能出现的。
四,牛河梁坛与冢在建筑形制上十分讲究方与圆的结合,有以为与后世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关,从而牛河梁遗址又可能具有祭祀天地的功能,如是,那么这应该就是史前时期祖先崇拜与天地崇拜相结合的反映。
牛河梁遗址群与坛庙冢有关的又一大内容就是积石冢墓葬随葬的玉器,一般以为,玉器是通神的工具,红山文化玉器从造型到出土状况都是对玉器的这种通神功能的典型反映。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一,从玉器造型看,红山文化玉器以神化的动物形玉器为主要类型。张光直先生曾列举了多种通神媒介。其中就包括在自然界曾经与人类长期和谐为伴的各种动物,以为“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最主要的助手就是动物。”红山文化玉器的动物形象,大都在写实基础上予以神化,特别是龙形玉的发达,都在显示其通神功能。通体贯通的斜口筒形器和非佩饰的勾云形玉,其造型或纹饰都可以从通神功能加以解释。
二,从玉器的出土状况看,红山文化有“惟玉为葬”的习俗。张光直以为“玉是自然生成之物,在沟通天地时有特殊作用。”通神要求和谐。人与神的沟通要求选择能达到高度和谐效果的媒介物。后世以玉的温润等特性解释人的德性的观念启示我们,古人对玉的重视,赋予其以通神以至礼德功能,正是识别出并看准了玉所具有的温润等特性,不同于或优于其他石料,最能体现和谐的观念,从而也能达到人与神沟通的最佳效果。红山文化墓葬中以非实用的玉器为几乎唯一随葬品而“排斥”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陶、石器的习俗,说明红山人对玉在通神中所具有的其他物质文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了非常执着的认识。也突显出与祖先神沟通这种精神生活在红山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王国维释“礼”(禮)字的创意为“以玉示神”,是独以玉器的通神导致礼的起源,这一精辟见解从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习俗中可以得到最为直接的实证。
三,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主要特征是都设有中心大墓,大墓主人随葬玉器的通神功能更为明确。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墓主人的左右手分别握着一件玉龟,是墓主人掌握神权的形象表达;新近发现的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随葬一件体形较大的玉人,玉人的双臂上弯贴于胸部,通体作运气状,应是一件正在作法的玉“巫人”的形象,玉巫人的出土位置又在人骨左胯骨部位,显然是墓主人随身系带的一件法器,暗示出墓主人很可能就是一个萨满的身份。这两座中心大墓位置都在冈冢顶部,墓穴凿入基岩,起台阶,尤其是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墓穴深凿于坚硬的变质花冈岩体,墓口长约4米,宽约3米,深达5米,墓穴的营造极为费时费工,突显出神权掌握者至高无上的的地位,这又是通神独占的表现,表明当时正在经历以“以玉通神为礼”为主要内容的跨进文明门槛的社会变革。
三.文化认同优先
“通神为礼”的观念不仅见于红山文化,在其它区域文明起源过程中也有强烈的反映。以与辽西并列为对中国文明起源起过主要作用的东南区和中原区为例:
良渚文化以玉琮为代表的发达的玉礼器和规范化的礼仪建筑,作为环太湖流域文明起源的证据,也都与通神有关。饰有兽面或人兽结合图像的玉琮,琮体外方内圆从中贯通的形制特点,刻纹图像中的人带羽冠、如兽面睁目露齿的体躯,都是追求高度神化的表现手法,无论器形特点还是饰纹,都在表明它们具有通神法器的功能。良渚文化以高台墓地与祭坛复合体为普遍特征的礼仪建筑,其通神祭祀功能与玉礼器是完全对应的。玉琮与玉钺在大墓中的共存则是集神权与军权于一身的表现。而这些因素又集中体现在良渚文化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良渚遗址群,从而形成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化,其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走通神为礼的道路与红山文化相近又各有特点。在中原地区,史前玉器虽不发达,然而构成其主要文化特征的各类彩陶器和小口尖底瓶,也被认为并非都是实用器,而更多是具有巫者通神使用的“神器”性质。苏秉琦先生就以为:“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半坡那种绘有人面鱼纹之类的彩陶,反映的已不再是图腾崇拜,已超越了图腾崇拜阶段,有些彩陶应属‘神职’人员专用器皿。”。最先倡导通神及其独占为中国文明起源特点的张光直先生,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有关祭祀遗址发现之前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是以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作为其重要证据的。他从仰韶文化彩陶等因素中归纳出巫觋人物特质与作业的阴阳两性、特殊宇宙观、迷幻境界、动物为助手、再生等7项特征,认为与近代萨满教相符合,从而以为仰韶时代萨满教证据是“全世界萨满教的最早形式”。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三大区在经济类型和文化传统上最初并不相同。中原区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以彩陶、小口尖底瓶到鬲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东南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以鼎、豆、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而东北区则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经济活动,以饰压印纹的筒形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表现为从经济类型到考古文化特征上的个性化差异。而且,三大区的这些个性化特征,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得以充分发展,而区域间的文化交汇,也恰在这一时期趋向频繁。
这是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它们之间却并不因为区域间的差异而相互排斥、相互冲突以致分道扬镖,而是在相互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无论是南北文化交汇所产生的“坛庙冢”,还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的“鼎豆壶”,它们恰恰分别成为后世礼制的主要内容。而且“坛庙冢”和“鼎豆壶”的初现最初都不在中原地区,却都在中原地区走向成熟并被历朝历代一直延续下来。
中国上古史上因文化互动而促成文明的诞生,其后必有某种更深层次和更强有力的共同因素在起作用。通神为礼的思维观念应该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共同因素。
通神为礼作为各区域文化彼此交流的基础促成文明起源进程,还可以从礼器在文化交汇中所起的作用加以证实。据研究,在文化交汇中各种文化因素的表现和作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如前述,仰韶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彩陶,特别是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在“北至大漠,南渐荆楚,西起甘青,东到鲁西”都有发现,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的全境;代之而起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其对其它史前文化的影响则主要为玉器,且传播范围更为广泛。如红山文化玉器传播的实例有:在冀西北泥河湾地区姜家梁的小河沿文化墓地中随葬有红山文化玉雕龙,晋南陶寺墓地随葬的玉器中,有典型的红山文化方圆形玉璧;山东省野店大汶口文化中期墓、江苏省青墩崧泽文化墓地、安徽凌家滩墓地和湖北省黄梅县塞东遗址也都有具红山文化特点的多联玉璧随葬。良渚文化的玉器传播路途更远,不仅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晋南陶寺文化,而且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陕北高原也发现了较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在相距数百里甚至上千里、相隔高山大川、而且往往属于不同系统的史前文化中,彩陶和玉器的迅速而畅通的传播交流,与诸考古文化其他与生产生活有关因素在相互交流中的局限形成显明对比,这显然与彩陶和玉器所具有的非实用性的通神功能有着直接关系,说明赋予思维价值观念的文化因素在文化交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优于其它物质文化因素。高炜在分析陶寺墓地礼器的多元性时就以为,《礼记》所记“礼尚往来”(《礼记·曲记》)就是“礼器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体现物”,在文化交汇中最为活跃的真实记录。
以上可见,通神为礼的观念可以超越诸多群体间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上的巨大差异,达到的是信仰的共同性,这种各区域文化间因观念形态的相同而向一起汇聚的趋势,已具有了最初的“中国”意识,苏秉琦先生称这种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的“中国”意识为“共识的中国”,“古国”时期的基本特征似也可以从中有深一步理解。尽管从文化认同到政治上的统一,还经历了数千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包括由古国时期的“共识的中国”到方国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中国”,再向秦汉一统帝国的“现实的中国”的过渡,但由于这种以通神为礼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认同,是在诸多群体、特别是文化源渊本来不同的群体之间反复的组合与重组中产生的,所以一旦实现,生命力极强,从而五千年前后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的“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为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以上从红山文化及其与相关区域考古文化的三方面比较分析中可见,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一统过程,还是中华传统初现过程,三者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影响极大。看来,对中华文明起源道路和特点的讨论,很有必要继续深入下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顺利完成》,《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30日。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与梁思永提出“东西混合说”的《小屯·仰韶与龙山》同时刊登于《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
安特生:《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地质调查所,1923年;(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4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新石器时代》143~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9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苏秉琦《我的一点补充意见》,《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
苏秉琦:《写在“中国文明曙光”放映之前》,《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10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巫鸿说:“‘庙’与‘墓’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崇拜对象的不同,前者的主要崇拜对象是‘远祖’,而后者则奉献给‘近亲’”(见巫鸿:《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99页)。
a刘晋祥在东山嘴遗址座谈会上的发言,《东山嘴遗址座谈》,《文物》1984年11期;
b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1期。
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第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郭大顺:《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的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张光直在论述良渚文化玉琮在巫师沟通天地人神的功能时曾讲到:“玉琮用玉作原料,很可能暗示玉在天地沟通上的特殊作用。玉在古代虽然在山水中都有发现,它与山的关系显然是特别密切的。”“神山是神巫上下天地的阶梯,则为山之象征或为山石精髓的玉作为琮的原料当不是偶然的。”(见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252~260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辑290页,中华书局,1959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5日第一版。
同,又见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36~1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7、23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2期;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邓聪编《东亚玉器.1》198页,1998年;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95页图六五11、15,108页图七九;大汶口文化出三联玉璧又见山东平阴周河遗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大学博物馆编〈山东大学文物精品选〉图版3,齐鲁书社,2002年);青墩遗址出二联璧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图一二.17;塞东遗址出三联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精华》第100页图七九.1,科学出版社,1993年。
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2期;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东亚玉器.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代艺术研究中心邓聪编,1998年
;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年2期。
高炜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1991年11月27-30日),《考古》1992年第6期。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4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