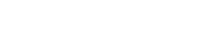原始巫术·玉器与红山社会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一、从地层剖面结构观察,处于西辽河流域腹心地带的科尔沁沙地系沙质土壤,由沙坨、沙沼、草甸组成,植被稀疏,腐殖质少,粘土含量极低,植被稀疏,蓄水保分能力差,有效养分甚微,即使在生态较好的地段,表层土壤下仍然是形成于全新世早期厚达数十米的流沙层,并且科尔沁沙地腹地沙质土壤易发生风蚀和风积,当环境恶化时,科尔沁沙地蔓延,处在其下风向的草原或耕地,也会因上风向发生风蚀而遭受风积,被流沙层覆盖甚至掩埋,敖汉旗北部、阿鲁科尔沁旗南部部分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部分特别严重的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
二、大兴安岭西南段与赤峰—敖汉黄土台地丘陵区,丘多馒头状、长梁状、浑圆状,丘顶平宽散立,局部积水成湿地、沼泽或小湖泊,比较适宜人类生存,根据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地域的文物普查来看,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在这一地域分布星罗棋布,说明全新世早期这一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生长旺盛,适宜人类在这一地域繁衍生存,只是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干扰作用,会导致不同时期出现景观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古文化出现频繁演替现象;
三、大兴安岭西南段—七老图山中低山地、大兴安岭西南段—努鲁儿虎山低中山地,山多尖顶状、长梁状,近山顶多峭壁,山坡平直,沟深谷窄且多峡谷,属于山地森林草原景观带,地势较高,并不适宜大规模人类群团的生存。
赤峰所在的辽西地区就气候而言,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东端,并与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辽西地区处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交接地带,是历史时期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而其核心区域是受环境影响大的科尔沁沙地,根据历史典籍记载,这一地域在历史时期是民族迁徙、人群互动频繁的地带。所以,这一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并不适合大规模农业耕作方式的开展。
二、特殊的经济模式
以红山文化为例:考古资料显示,红山文化遗址群多分布在大兴安岭西南段与赤峰—敖汉黄土台地丘陵区的二级阶地上,而红山文化时期人类活动的遗物多散见在生土层之上的黑土(沙)层中(古土壤层),而黑土(沙)层实为植被的腐殖质和沙土的混合物,是科尔沁沙地上曾经有过繁茂植被的有力见证,证实了早在史前阶段的科尔沁沙地,植被茂盛,生态环境还未受到严重破坏。例如: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层都存在于灰色土的堆积中;敖汉旗三道弯子遗址存在于黑灰土之中;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北沙丘中的5个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在灰褐色沙土层中;林西县沙窝子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包含在第二层的黑沙土层内”;西拉木伦河北岸的海金山遗址的文化层为黑土层;科左后旗的布敦哈日根等14处红山文化遗址都出土于黑沙土中;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中出土了大批动物骨骼,考古工作者认定“有野猪、鹿类、黄羊、狗獾、松鼠、狐狸以及犬科和洞角类动物。……这些动物全是现代东北动物系中的山地森林动物。数量上以偶蹄类为多,未见草原奇蹄类动物”。巴林左旗位于科尔沁沙地西北缘,距今约6000年左右。此时尚有大量森林环境中生存的动物,而不见有草原类动物,从动物可大范围移动的角度分析,科尔沁沙地大部分地区尚不属于荒漠草原地带。
这次调查揭示了科尔沁沙地的特点和地表状况以及往复变化的内在机制:当气候条件变坏、人类生产活动加剧时,地表植被破坏,沙地面积相应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迫使人类退出,于是赋沙地以“休息期”,自然状况又逐步改善。同时也印证了赵志军研究员的推测,繁盛的红山文化时期,是人类对科尔沁沙地自然植被进行的第一次“大破坏”,沙地则在此后经历了自身历史上第一个大扩张期。
通过这次取剖面分析,即使在科尔沁沙地逆转期时,景观比较好,植被茂盛,也不适宜于耜耕农业耕作方式的进行,因为沙地位于大东北的低凹地带,形如“盆底”,地下径流汇聚于此,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即使在核心地区,掘地尺余,也可发现水汽浸漫的湿沙。而这一地区的降水量集中在每年的7—9月份,降水密集时,就会在沙地腹地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泡子,不利于粟作植被的生存,并不适宜大规模人类群团的生存,但这些水泡子恰恰为生活在其周边地区的人群提供了渔猎的可能,因此也为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提供了资料,这一点亦可从红山文化遗址中所见生产工具中发现大量渔猎工具得到佐证。
红山文化时期正值大暖期气候最适宜时期,亦是科尔沁沙地全新世早期第一次逆转期,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较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分布密集,分布范围扩大,并且这一时期生产技术与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进入了西辽河上游第一次农业生产大发展时期,但上述文化特征并不表明当时人口密度大,数量多,宋豫秦博士认为是撂荒轮作式粗放型农业活动的结果,是很有见地的。以林西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在遗址中出土较多野生动物骨骼,如熊、赤鹿、马鹿,具有较多野生特征的猪、羊等以及细石器和打制石器较发达,加上居住遗址文化堆积普遍较薄所反映的定居不稳定性等方面看,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很大。
三、红山文化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模式比较研究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他界定的中国北方是指黄河流域而言,由于故而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氏族意识浓厚,祖先崇拜盛行。)。李安宅:由着私巫变成共巫,及为公巫,便是俨然成了当地领袖,领袖的权威越大,于是变为酋长,变为帝王—酋长帝王之起源在此。)
红山文化时期本身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经营模式,决定了与中原地区的巨大差异。中原地区,地势平坦,黄土疏松,雨量集中于夏季,适合大规模协作的粟作、稻作农业,加之陆上交通方便,易于产生共同的意识,并需要强大的军权、王权来维系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在同一时期(或稍晚阶段)中原地区的凌家滩、良渚文化玉器则出现了大量能反映王权的玉器。而在红山社会只是用宗教(而其经济模式根据考古资料及实地调查信息所得,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而辅之以撂荒式农业经济模式,对自然的依赖性较中原地区强。)来维系的社会群团。
红山文化玉器制玉工艺达到极致是在红山文化晚期,表现浓烈的宗教色彩,未脱离北方所特有的自然神崇拜。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经济模式有直接关系。
张光直先生“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换……从史前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
通过宗教仪式行为来掌握和决定政治行为的。
1、印有篦纹和之字形压印纹的粗质褐色平底陶罐。
2、含有磨光石斧、石墨棒与打制细石器和小型尖器的石器群,这类遗物指向农耕、畜牧和渔猎的混合生业。(这是张光直对新乐文化的阐释)
萨满式的巫术,即巫师借动物的助力沟通天地,沟通民神,沟通生死,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
在原始社会后期,宗教仪式的主办和宗教场所的兴建,可以说是组织和影响群众的最方便的手段,这种凝集力有时连生产和战争也难以比拟,在从事以宗教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氏族的上层集团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
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的修建与管理,大型祭祀礼仪活动的组织,都说明“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维系力量是什么呢。
张忠培先生认为,王权产生的前提是军权,而在凌家滩、良渚文化中均能通过器物、聚落等外在形式体现军权力、王权,而红山社会的各种表象特征均未能体现,可以说得通的是特殊地理环境、特定的经济模式影响下的原始宗教,而玉器则是宗教维系社会组织正常运作的最佳手段、媒介。反过来看,红山文化玉器中多动物形器,本身即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特征。
玉器是神权强化的物化形式。
原始宗教是支撑原始社会的框架和创造史前文明的力量。
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末叶,就精神领域而言,原始宗教的辉煌,分明就是文明的形成,国家建立的必要条件和保障,成为文明诞生的催化剂和助产婆。在文明出现的前夜,氏族贵族利用人们对原始宗教的虔诚与崇拜,最终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红山文化古城、古国出现,文化遗迹中阶层分化,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的局面。这一时期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巫师、巫术的盛行,多神教向一神教靠拢,大型礼仪建筑的矗立,出现了天、地、神、人合一的高级宗教思想意识,它昭示着原始宗教光辉的顶点。原始宗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当时部族首领兼作巫师,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其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因巫师是巫术的操作者,又是天与地、人与鬼神的沟通者,还是当时社会知识的创造者、积累者,很多文明因赢是由他们攀提及传播的。只有这种身兼诸能的半人半神的人物,才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召一切、指挥一切、执行一切,完成进入文明时代的这一历史伟业。
原始宗教发挥著组织、协调、统率社会的特殊作用。氏族贵族首领,凭借着宗教的神奇魁力把自己打扮成半人半神的圣体,树立起庄严的权威,聚敛着社会财富,打碎了氏族社会平等、博爱的秩序,建立起一个阶级分明、王权日趋发展的社会政治实体。
从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信息来观察,辽西地区亦有别于中原地区及周边地域的社会发展模式:
1、辽西地区受其特殊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的影响,历来作为古人类迁徙的地域,素有“辽西走廊”之称。
2、历史时期,在辽西地区存在过的北方民族在这一地区多建立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如:契丹早期社会古八部,根据研究所得,是用原始宗教(萨满教)来维系的部落联盟组织,只是后来受到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逐步走上游牧封建制社会。
从历史时期各个文化区域宗教传统的发展来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巫教随着最高政治集团核心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减少,其职能亦在逐渐减弱,中古时期已逐渐流入民间。而萨满教随着畜牧业的兴起、发展以及向农业生产方向的不同程度的转变,加之大北方系统诸民族间的文化冲击与碰撞,依然在中国北方巫王合一、巫王合作的政权体系下扮演重要的角色。
通过上述阐释可知,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前期至红山文化后期积石冢石棺墓中埋葬的死者应该是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内的祭司即萨满巫师。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前期墓葬规模、随葬玉器来看,这一时期萨满教信仰在辽西区应处于初创阶段,而到了红山文化后期,当时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人口剧增,进入比较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而红山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巨大系统,在文化发展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以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自身农业经济、狩猎采集经济并重的前提条件下,同时接受中原发达的农业文化带来的各种基因,在宗教信仰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本区域原初形态萨满教在发展进程中吸收了来自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先进因素,这时期一些族体中的萨满巫师成为了氏族上层成员,有的兼有部落首领身份,萨满不同程度地充当了部落间军事与政治事务的裁决者与执行者的角色,既掌握了神圣的宗教权力同时又掌握了世俗权力,有向巫王合一型转化的趋势。正如张忠培先生在分析阜新胡头沟中心墓时说:“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执掌军权和既掌军权又握神权的这类新人,已是些颇具权势的显赫人物。”